上海与北京:现代性之梦与家园之梦
北京和上海,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,在百余年的文学作品及论著中被赋予了很多意义,也被寄予了不同的诉求。在研究上海文学时,张鸿声老师认为文学赋予上海的最大意义就是现代性。在《文学中的上海想象》一书中,张鸿声老师这样写道:20世纪文学中的上海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,甚至表现出某些现代性修辞策略,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,以此构成了“文学中的上海”强大的现代性身份。
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学作品中,对上海的发达和现代化的夸张表述比比皆是。除了描写的物质场景与巴黎、纽约无二外,连作品中人物的身体特征也非常西方化,高鼻子、短发、嗓音沙哑,还有因大量户外运动而产生的淡淡的褐色皮肤。与之相对的,那些不符合现代性的特性,如东方性、乡土性、地域性等,便在文本中被遗忘、淡化或是略去,因为这些妨碍了对现代性的表达。
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修辞堆积,一方面是对非现代性事物的忽略,文本的“上海”与作为地域的实际的上海呈现出极大的差异,个中原因是什么?张鸿声老师认为,在世界主义背景下,近代中国有一种对“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”这一民族“想像的共同体”,而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国家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。简单说来,就是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一直有一个现代化的梦想,而对上海的叙述承载了这个梦想。
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写过一部小说叫《新中国未来记》,书中用未来完成时,写1952年上海召开世博会:“那时我国决议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,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,不特陈设商务、工艺诸物品而已,乃至各种学问、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,处处有论说坛、日日开讲论会,竟把偌大一个上海,连江北,连吴淞口,连崇明县,都变作博览会场了。”世博会作为一个国家强盛到顶点的标志,梁启超写1952年上海召开世博会,就是希望在1952年国家现代化已经达成,中国已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。其实,在全世界范围,落后国家急欲获得现代性是一个普遍情况。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·赫茨尔1902年写了《古老的新国家》,也是用未来完成时,写了犹太国家将在1920年完成现代化大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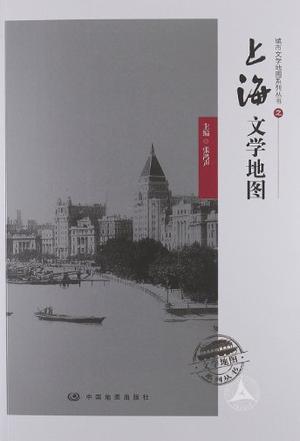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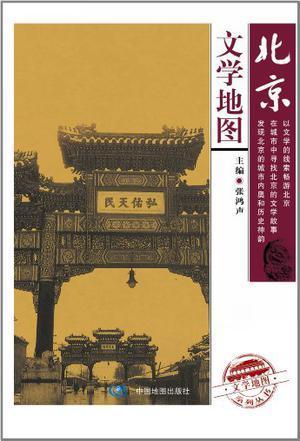
与上海被赋予现代性的意义不同,北京在20世纪中的不同的时期,分别被赋予了帝都、家园、社会主义中心与国际化都市等意义。北京自金代建都以来,800余年的都城历史,使得“帝都”的形象深入人心,林语堂就认为北京是“深具着伟大的帝王气象”。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中心已从北京转移至上海,上海发达的现代性给新文化人带来了事业的发展、生活的便利,但是作家内心的归属却往往体现在对北京的情感之中,对北京的向往与怀恋渐至浓烈。老城市低矮的建筑、花木、湖泊、风俗等非常符合人们对家的感觉,北京“家园”的意义逐渐被建构起来。30年代的文人一再谈到北京“住家为宜”,甚至南方等地的文人也将北京视为归属。周作人写道,北平于我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,与我很有些情分。值得注意的是,尽管北京一直是知识分子乐于表现的地方,但由于已是旧都,30年代的北京相当破旧,有了“废都”的意味,徐志摩曾将北京指为“死城”,前门就像一个“骷髅头”。
进入50年代以后,北京又被赋予了社会主义中心的意义,乃至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中心。文学作品中对北京的古典性叙述转为现代性叙述,城市空间的不同选择体现出意义的流变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中轴线描写的变化,古典性叙述喜欢写纵向的老中轴线,即天安门-故宫-景山一线;但50、60年代的叙述更多是横向的中轴线,即长安街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还大量写到北京展览馆(原名“苏联展览馆”),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国际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物质构成,通过描写它可以把北京塑造为一个充满国际色彩的社会主义中心。90年代后,北京“国际化都市”的意义日渐凸显。在比较典型的邱华栋的作品中,有很多这样对东二环、东三环的描写,“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,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,国际饭店、海关大厦、凯来大酒店、国际大厦、长富宫饭店、贵友商城……”(《手上的星光》)这些大量没有民族意味的、泛国际化的物质符号,把北京描写成一个与纽约、休斯顿没有区别的城市。
相对于上海现代性的梦想,北京承载着人们对家园和传统的眷恋,张鸿声老师认为,北京的意义可能会更恒久一些。因为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,人们对自我身份、文化身份的寻找会愈加强烈,对老中国的传统愈加眷恋,对传统家园的寻找愈加迫切。“中国人借上海表达现代性特别猛烈,但是借北京表达家的诉求会更恒久绵长。”他说。




